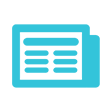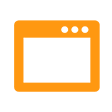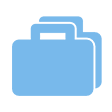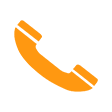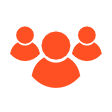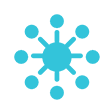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检察调研
当前位置:首页 > 检察调研
某国有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某,与某建筑公司负责人李某交往密切。2010年以来,张某多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李某的公司在项目融资上提供帮助。2012年5月,张某之妻吴某参股并管理的某合伙型基金出现股权投资风险,不能按期兑付投资人本息,张某提出将该基金所投资的有风险的股权出卖给李某,价格为该基金需要兑付投资人的本息金额420万元,李某表示同意。2012年8月,李某以42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基金持有股权。经评估,该基金持有的股权交易时的市场价值为140万元,李某的支付价格实际溢价280万元。因吴某实际控制的某咨询公司是该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按该公司投资比例,吴某实际获得收益17万元。
【分歧意见】
针对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以及如何认定受贿数额,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理由是:股权交易的双方为李某公司与合伙基金。420万元的交易价格经双方沟通确定,虽然该价格高于股权当时的价值,但溢价处理属股权投资的常见情况,不能排除正常投资行为的可能。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为特定关系人吴某实际所获的收益17万元。理由是:受贿数额的计算,应以行为人实际获取的财产性利益数额为准。李某在张某授意下,以420万元价格收购基金持有的股权,但股权溢价的280万元需要在基金内部按照投资协议分配;吴某的公司除按比例实际获利17万元外,其余部分为其他投资人所有,不应计入受贿数额。
第三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应按照股权价值与交易价款的差额280万元认定。理由是:在性质判断上,本案名义上虽是股权交易的市场行为,但由于转让股权是张某向李某提出,且张某之妻吴某是基金的投资人和实际管理人,故双方行受贿的主观故意明显。在数额认定上,双方确定了交易价格,溢价款也在双方的合意范围内。股权交易完成,则受贿已经既遂;吴某对280万元溢价款向投资人再分配,属于既遂后对赃款的后期处置,不影响犯罪数额的认定。
【评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从行为定性来看,溢价转让股权行为的本质是权钱交易。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即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案中溢价出卖股权的行为,具有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从受贿人的角度讲,张某之妻吴某是合伙基金的投资人和管理人,二人是利益共同体,基金经营状况直接决定其家庭经济收益。张某为化解吴某管理基金面临的兑付风险,明示李某出资收购基金所投资的股权,其以权谋利、以权谋私的意图和行为明显。从行贿人的角度讲,行贿人李某并未对目标企业的经营状况、股权价值进行尽调、评估,而是按照基金需要兑付投资人本息的金额确定股权收购价款,其行贿的意图明确。
因此,本案股权溢价收购行为,不是正常投资行为,实质上是以股权交易为掩盖输送利益的行受贿行为。张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无疑。
从数额认定来看,受贿既遂后的财物处分不影响数额认定。按照基金投资协议,吴某实际获得17万元的收益,但这并不能否定280万元的受贿数额。
本案认定受贿犯罪数额,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明确行受贿双方对犯罪数额的合意范围;二是准确判断受贿既遂的节点,受贿既遂后,行为人对财物如何处分并不影响数额认定。从双方的主观合意来讲,280万元溢价款就是行受贿双方的犯罪对象。股权交易溢价的280万元是李某对张某职务行为的报酬,对此双方具有明确一致的认识,主观上均不排斥股权溢价收购行为的发生,溢价的280万元在双方合意范围之内。
从犯罪既遂的角度来讲,张某之妻吴某是基金的投资人和管理人,对基金账户内的钱款具有控制、管理的权力。因此,当李某的收购款支付到基金的银行账户,吴某即取得对280万元溢价款的控制,此时犯罪已经既遂,受贿数额亦应当以溢价的280万元计算;而吴某在基金内部对溢价款进行分配处置,包括其本人最终分得17万元,属于受贿既遂后对财物的处分、支配行为。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受贿后赃款用于单位支出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但可以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因此,本案的受贿犯罪数额应认定为280万元,溢价款的分配暨实际所得应当作为量刑情节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