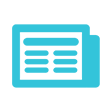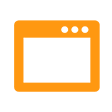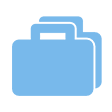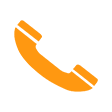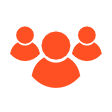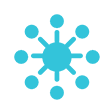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检察文化
当前位置:首页 > 检察文化
小时候就有一个行侠仗义的梦想,高考填报志愿时便义无反顾地填写了那个梦想中的法学殿堂,四年后沐浴着计划体制的春风顺理成章的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穿上了心仪已久的草绿色制服(那个年代的检察服是草绿色的)。日月轮换,拉风的大壳帽和红色的肩章随着我飞扬的青春一起隐进了岁月的深处,张扬的绿色制服变成了深蓝色的西装,浓密的黑发被时间和操劳修理的日渐稀疏并挑染出缕缕的斑白,但梦想的大门总是没经任何现实的猛烈敲打,便在我的面前豁然打开。无论是在控申处时办理申诉案件、接待群众来访,还是二审监督处时办理上诉、抗诉案件,以至于现在从事的公诉工作,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深爱的刑检业务,总可以在沉静与思索中为受害者擦去委屈的泪水,在真诚地倾听与热诚地析说中为沉冤的浊流打开一道出口,在控诉与激辩中使自己的侠肝义胆得到妥当的安放。于是我经常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上苍对我的眷顾,感谢父母、亲人在困顿中倾尽全力对我学业的支持,感谢我生命旅途中的每一路口遇到的每一个相携相伴的战友,感谢对我包容理解的领导允许我在广阔自由的天空放飞自己的理想。
多少个挑灯夜战的时刻,多少次面红耳赤的争论,多少回法学知识的反复咀嚼,只为一个案件中此罪与彼罪的定夺,只为一个法律适用的妥当与否,只为在纷繁复杂的证据中去伪存真,编织成打击犯罪维护法律尊严的正义之网。非常难忘自己与三个战友连续奋战六天,舌战36名辩护人的情景。那是自己第一次独立带兵承担那样重大的案件,因为紧张,因为兴奋,更因为背负着重重的责任和嘱托,连续六个夜晚无法入睡,睁眼闭眼全是案件的事实、证据,全是白天庭审的回放镜头,直到庭审的结束,精神彻底放松后才感到无法言说的困倦,回到家顾不上吃饭,倒头便睡了十二个小时,那十二个小时是我从未体会到的最香甜、最放松的休息。
也非常难忘自己到公诉处后接待的第一个被害人家属,她年仅20岁的儿子在一次聚众斗殴案件中被害,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案件的主犯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的妈妈接到判决书后,便头上缠着写满“冤”字的白布条,手捧被害人的遗像,跪倒在我院接待室的门口。听到消息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接待室,当我亮明身份,将她扶坐在椅子上时,她全身颤抖着痛哭失声,我知道此时再多的语言都无法劝慰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但我也知道,法律的公正就在于他平等的要求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递给她一个纸巾,为她倒了一杯热水,紧紧地坐在她的身旁,拉着她的手,等待着她慢慢地恢复平静。当悲伤的母亲开始诉说她的痛苦和要求时,我非常认真地听着,并不时的与她交流我的感受,也许是因为同为女性的缘故,我非常能够体会她当时的心境,我从案件的事实,讲到法律的适用,又讲到了我所了解到的类似的判例,最后又讲到了她以后的生活……,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出门前,这位母亲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告诉我她的心里豁亮多了。这是我第一次切身的体会到:也许我没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别人的痛苦,但我最起码可以做到尊重他们抒发痛苦的方式,以我所学的法律知识,解除他们对法律的误解,彼此的尊重是沟通的第一座桥梁。
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津巴多曾经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恶,并不是少数“坏苹果”犯下的,相反,而是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极端行径。二十多年的刑检工作让我对津巴多的话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也因此,对普通人的极端行径多了一份关注。2010年初春,在我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件:一个中年男子骑电动自行车沿公路前行,与同样骑电动车的某中年夫妇发生擦碰,双方发生口角,继而大打出手,中年妇女见其夫渐入劣势,便火速回家喊来其子助阵,中年男子不敌父子二人的共同殴打,命归西去。最终父子二人共同锒铛入狱。接到案件的判决后,我并没有因为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感到丝毫的宽慰,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是不是还会遇到同样的案例。放下判决,我很快写了一篇《小纠纷引发的人命案》的新闻稿,通过办公室送交相关媒体发表。在稿件中我特别提醒市民遇事要冷静,不要等到出现极端行为引发恶果后再追悔莫及。
从事刑检工作,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常人无缘触碰的领域,看多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我的人生从此多了一份从容和淡定。领略了生命中更加丰富的色彩,不仅习惯于夺目的艳丽,也可以接受无法回避的灰暗,心胸从而变得更加豁达和宽容。我选择了这份职业,也因此对其充满了更深的敬畏,其间不仅渗透着对这份职业的深深热爱,还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于是我常常自恋的认为自己就是梦中的那个侠女。